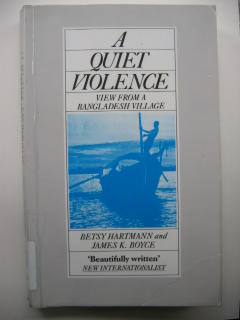抽苔是啥?
植物的「抽苔」
抽苔就是開花的意思,植物開花不外就是為了傳宗接代,什麼時候植物會開花呢?
第一個可能當然就是「時候」到了,每種植物都有其生命週期,從種子下地到成長發育到最後的開花結果,都有其一定的順序,那植物為何會知道現在要該發芽還是該長大還是該開花呢?基本上植物大多已經將這樣的程序預設在他的基因裡了,而起動的機制就在大自然的溫度與日照時間,所以可以將植物想像成身上佈有許多細小的微電腦與雷達,時時刻刻接收著大自然的訊息,按部就班的完成他的生命週期。
另一個可能就是環境太過惡劣,但還未糟到活不下去的地步,所以植物就會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,因此會提早開花結果,這部分與我們人類很像,自己未竟的心願便希望下一代來替我們完成,說好聽點就是「孩子,我希望你比我強!」因此會把畢生最好的東西全留給小孩,植物也會這樣,快死的時候就將希望放在下一代,便用最後的力氣,將養分全都往種子送,為的就是繼續將基因流傳下去。最近我發現園子的玉米長不到一公尺高便抽苔了,我想應該是氣數已盡,畢竟是受到連續兩個颱風的虐待,存活下來已不容易,真苦了他們,不過我更擔心的是能不能結果,因為我只看到雄花開,雌花能否順利授粉並累積足夠營養長成玉米?也只能繼續觀察,有新的消息在跟大家報告囉!
另一個提早抽苔的是一棵芥菜,我想原因應該也是因為環境不好的緣故,但確切的不好到底是什麼,我也無從判斷,有可能是缺肥,也有可能是缺水,也有可能是因為土讓質地太密太緊,都有可能,但幸好只有一棵是這樣,其他的芥菜仍在努力生長。不過有人知道芥菜花是否好吃嗎?不過我更想要的是把這樣的芥菜種子留下來,看看明年會不會生長。
植物對生長環境不好還有另一種反應,就是「未老先衰」,明明個頭還小,葉子卻老到不行,「老」意味著顏色深沈,質地脆硬,園子裡有些荷白(老闆說是日本種的小白菜),從下地到現在沒長大過,唯有葉子越來越深,也越來越硬,台語念做「ㄍㄨㄚ ㄎㄧˇ」有趣吧!我們只有老的時候心態會像小孩,到沒聽說有小孩會因為環境不好而長得一副老氣橫秋的模樣,不過在人類社會中環境不好的人看起來會真的比較「ㄘㄠˋ老」倒是真的。